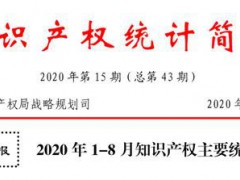科技發展放大了方法專利侵權的特殊性,由此催生出一種新型侵權,即多主體實施方法專利侵權。為了應對此類侵權,美國法院確立了“控制或指導”標準,而我國司法實踐則總結出“不可替代的實質性作用”規則。然而,囿于“單一實體規則”的限制,建立于專利直接侵權基礎上的現有規則,逐漸產生與技術發展不相適應的困境。從法解釋視角分析,應將多主體實施方法專利行為定型化為一類適用間接侵權的例外事由,并細化構成要件以保證司法裁判的規范性。
科技發展與法律規則相互交錯下的空隙滋生了一種新型侵權樣態,即多主體實施方法專利侵權。靜態的法律規范總是遲滯于動態的社會現實,國家強力的適時介入可以調適法律的僵硬性,然而科技的迅猛發展使得法律的滯后屬性加速演進,甚至出現法律制定者根本無法預期的技術形態。在通信軟件、物聯網、生物制藥等領域,一種多主體、分布式、跨地域侵害方法專利的行為正在迅速蔓延,掣肘于方法專利侵權的特殊性,現有規則無法消解多主體實施方法專利侵權難題,亟須構建符合我國國情的侵權判定路徑。
一、邏輯起點:多主體實施方法專利侵權的概念及特殊性
(一)多主體實施方法專利侵權的概念
多主體實施方法專利侵權又被稱為方法專利分離式侵權、方法專利拆分侵權,是指缺乏共同意思聯絡的數個主體,分別連續實施方法專利的若干步驟,每個主體的行為都不足以覆蓋方法專利的全部技術特征,但整體行為的疊加侵害方法專利權的行為。多主體實施方法專利侵權問題肇始于美國判例法,起初發生在傳統制造行業,企業家們通過分散方法專利實施步驟的形式逃避責任,而傳統制造行業的實體性通常需要多主體之間進行有效的犯意溝通,因此早期美國法院傾向從共同侵權的角度判定多主體承擔連帶責任①。
網絡技術的發展和專利社會分工的細化,使得專利權突破原有的地域性,無形中放大了權利的效力范圍。多主體借助互聯網軟件等新興技術實施方法專利侵權更具隱蔽性,通過設定編程或者程序性語言的方式代替真實的犯意表露,間接操縱終端用戶實施方法專利的全步驟以轉嫁責任,共同侵權的事前聯絡要件逐步虛化。此種境況下,民法理論的共同侵權責任出現適用障礙,無法提供及時有效的權利救濟[1]。那么根植于專利權建構的專利制度能否防治多主體實施方法專利侵權問題?對此,美國Lemley教授作出過經典論述: “專利直接侵權要求單一主體執行方法專利的全步驟。某一主體僅參與但未完成方法專利要求的整個流程,只能依據專利間接侵權追索責任,而間接侵權在制度設定上又必須要以直接侵權為條件。[2]”專利侵權保護制度在應對這一問題時陷入自相矛盾的尷尬境地。
科技的發展使得隱藏的法律漏洞凸顯,形成侵權的可乘之機,有學者認為技術發展與專利保護制度不周延是多主體實施方法專利侵權問題的癥結所在[3]。事實上,專利保護制度不周延除受到法律滯后性的干擾外,深層原因是方法專利的自身特殊性與現有制度安排的不相適應。
(二)多主體實施方法專利侵權的特殊性
我國專利侵權法律制度大致依循產品專利的保護思路構建,對產品專利和方法專利實行區別性保護,“專利產品”采取“強保護”,“專利方法”采取“弱保護”[4] ,方法專利的諸多特性缺乏充分的立法考量。橫向比較產品專利與方法專利可以看出,多主體實施方法專利正是基于方法專利特殊性衍生的一種侵權類型。
首先,兩者的客體表達形式不同。產品專利的客體指向特定物品,追求物品物理屬性或者化學特性的改變,依賴一定載體表達。方法專利指的是為實現特定目的的一系列步驟,最終以某種非物質性結果表達,比如制藥方法、計量方法等。與實施產品專利侵權所要求的生產線、生產設備等高門檻不同,方法專利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尤甚,相對較低的外部識別程度導致“搭便車”現象頻現,即使普通消費者也可以輕而易舉地實施方法專利 全步驟,更遑論多個主體分別執行方法專利的某個流程。
其次,兩者的權利效力范圍不同。產品專利的效力范圍采用“結果主義”,只要涉案產品被實際實施,不考慮產品實施主體是單個還是多個,也不論采用何種方法生成涉案產品,都將落入產品專利的保護范疇。而方法專利采用“行為主義”的效力認定方式,權利要求書記載的方法步驟技術特征是唯一的侵權判定依據。當多個主體分別實施方法專利某個步驟,而整體又契合方法專利全部技術特征時,雖然事實上方法專利受到侵害,但受制于專利直接侵權主體的單一性要求,法律層面會出現直接侵權的適用不能。
再次,兩者的侵權意圖聯絡不同。在產品專利侵權中,行為人須遵循一定的技術原理,將產品所需的零部件進行組裝,最終的產品性能或者屬性與權利要求書記載的技術方案一致。多主體實施產品專利侵權時,理應事先聯絡并分工配合,僅僅是多個單獨行為的客觀巧合導致侵權,幾乎無法實現。與之相反,方法專利強調的是前后步驟的銜接與配合,不具有強烈的技術依賴性,甚至在某些特定的領域,一般消費者也能依據生產廠商提供的手冊,無意識地完成方法專利,缺少完整的意思聯絡不影響多主體實施方法專利侵權。
最后,兩者的舉證難易程度不同。“誰主張誰舉證”是民事訴訟的舉證原則,當其作用到專利侵權的發生場域下,要求權利人證明被告行為覆蓋了涉案專利的全部技術特征。產品專利權人通過拆解或者鑒定涉訴物品的內部構造或者運行機理就可以達到舉證效果,而方法專利權人則要深入生產車間進行現場調查,且不論缺乏實體狀態的方法專利侵權不易覺察,僅就實施方法專利的不可重復性就足以困擾權利人的舉證活動,當多元主體實施方法專利侵權時,時空的阻隔進一步加劇侵權舉證的難度。
二、經驗梳解:多主體實施方法專利侵權判定的實踐
(一)美國多主體實施方法專利侵權判定的演進
1.地區法院兩種標準的博弈
美國1952年《專利法》第271條規定了直接侵權與間接侵權兩種侵權形式,專利直接侵權采用嚴格責任原則,專利間接侵權則要求行為人主觀故意,并以直接侵權作為成立前提。專利間接侵權細分為專利誘導侵權和專利幫助侵權。囿于專利間接侵權的從屬性,美國法院起初傾向于擴張性解釋直接侵權應對多主體實施方法專利侵權問題,并在此基礎上延伸出兩種判定標準,分別為“代理關系”(agency relationship)標準和“某種聯系”(some connection)標準。“代理關系”標準脫胎于被代理人與代理人之間的強關聯關系,即實施方法專利侵權的數個行為人,如若一方對其他方施加類似于代理關系的控制或指導,就能夠認定占主導地位的行為人侵權。與“代理關系”標準所要求的緊密聯系不同,“某種聯系”標準認為,實施方法專利侵權的多主體無須具備強烈的關聯性,當行為人與其他主體進行直接接觸或者相互合作時,就可以認定構成侵權②。
美國聯邦巡回法院對兩種標準的態度不斷反復 ③,直到2007年的BMC案,聯邦巡回法院在“代理關系”基礎上總結出“控制或指導”(control or direction)標準,認為“只有一方對他方表現為‘控制或指導’才能繼續考慮是否構成侵權”④ 。盡管聯邦巡回法院承認“控制或指導”標準依然難以全方位保護專利權人利益,侵權主體可以通過事先約定的形式規避責任,但相對于“某種聯系”標準對權利主體的過度優待,限制法院的恣意裁判以防止專利權濫用是非常有必要的。
2.剛性“控制或指導”標準的確立
BMC案之后, “單一實體”(single actor)規則和“控制或指導”標準成為判定直接侵權和方法專利侵權的兩條路徑[5],即要么行為人獨自實施方法專利的全步驟,要么其對方法專利整個流程的實施具有控制力或者指導力。事實上,聯邦巡回法院拋棄“其他聯系”標準而選擇“控制或指導”標準,很大程度上體現了美國法院當時所奉行的司法政策,即傾斜性保護社會公共利益,防止不當擴展專利權范圍而引發濫用。但由于缺乏明確要件的 支持,“控制或指導”標準的適用幅度取決于法官對案件事實的把控,司法政策指引下的法官逐步偏離專利權與公共利益的平衡點,“控制或指導”標準的適用漸趨嚴格化。
在Muniauction案中,美國聯邦巡回法院表示,“控制或指導”標準的判斷不具備任意性,只有某一主體控制或者指導其他主體實施方法專利的每一個步驟,該主體才需承擔侵權責任⑤。隨著多主體實施方法專利侵權案件的不斷增多,BMC案和Muniauction案所確立的剛性“控制或指導”標準不僅沒能實現侵權糾紛的消解,反而因其過度僵化在實踐中引發很大爭議。有學者指出, 自BMC案和 Muniauction案之后,專利權人很難在多主體實施方法專利侵權案件中勝訴[6]。
3.專利誘導侵權規則的適用
“控制或指導”標準的理論局限迫使美國法院尋求新的應對之策。2012年Akamai案,聯邦巡回上訴法院不再固守直接侵權的判定路徑,將多主體實施方法專利侵權認定的焦點轉向專利誘導侵權 ⑥。
依照遵循先例的司法原則,美國誘導侵權的司法適用從屬于專利直接侵權,不具有單獨適用的法律基礎。聯邦巡回上訴法院并未否認這一既有規則,而是對作為間接侵權前提的“直接侵權”涵義作了新注解。聯邦巡回上訴法院認為,只要方法專利的全部技術特征被實施,直接侵權在客觀層面就已經成立,雖然多主體侵權不契合“單一實體”規則,無法利用專利直接侵權加以規制,但這并不影響專利引誘侵權的認定。
4.“控制或指導”標準的軟化
2014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再次推翻Akamai案確立的誘導侵權適用規則,重申“除非存在單個主體實施直接侵權,否則不能認定引誘侵權的成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專利權的控制范圍由權利要求書記載的所有要素限定,由此向社會公眾傳遞明確的權利信息,任意擴大方法專利的保護邊界會侵蝕專利權的壟斷性。
聯邦最高法院在否定誘導侵權的獨立性后,同樣認為基于 BMC案和 Muniauction案確立的“控制或指導”標準過于剛性,“狹隘地限定了專利直接侵權的控制范圍”,難以實現專利權人與社會利益的平衡,要求聯邦巡回法院軟化“控制或指導”標準。聯邦巡回法院重新解釋了“控制或指導”標準的邊界,“被控侵權人實施方法專利的步驟時,如若以參與活動或者獲得利益為條件,明確實施方法專利的方式或者時間,就應認定為直接侵權”, 事實上放松了“控制或指導”標準的適用彈性。
在司法裁判中,軟化的“控制或指導”標準可操作性和靈活性更強,但其判定重心依然停留在主體間關聯性上,當沒有足夠密切的關系使一方行為可歸因于另一方時,就無法彌補現有規則的漏洞,因為其無法保護專利權人和無辜第三方的利益 [7]。
(二)多主體實施方法專利侵權判定的本土解讀
近十年,我國多主體實施方法專利的侵權案件顯著增多,與此同時,相關方法專利的配套法律卻供給不足,雖然專利法明確保護方法專利的使用以及延伸性保護依照方法直接獲得產品,但并未細化方法專利的使用方式和產品延伸性保護的范圍。司法實踐迫切需要應對多主體實施方法專利問題的可適用性標準,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第159號指導案例,借助敦駿公司訴騰達公司案(以下簡稱騰達案)⑦,澄清了多主體實施方法專利侵權的價值傾向和裁判思路,并提出“不可替代的實質性作用”規則。
在騰達案中,被訴方騰達公司以生產經營為目的,制造和銷售固化了方法專利實質性內容的涉訴產品,使得終端用戶實際實施了方法專利的全步驟,而被訴方騰達公司的制造和銷售行為,既不符合專利直接侵權所要求的覆蓋全部技術特征,也難以契合幫助、引誘侵權的法律規則。作為涉案方法專利侵權的始作俑者,騰達公司假借消費者實施侵權的行為具有非難性,認定其不承擔責任并非司法公正的應有之義。因此,最高人民法院認為,網絡通信領域多主體實施方法專利的侵權判定,須綜合考慮網絡環境的特殊性與專利權人的正當利益,當涉訴主體為生產經營目的,將專利方法的實質性內容固化在侵權產品中,就能夠以該行為或者行為結果對專利權利要求的技術特征被全面覆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實質性作用,認定被訴方構成方法專利侵權。
“不可替代的實質性作用”規則適度突破全面覆蓋原則的約束,將“固化方法專利的實質內容”解釋為“實施方法專利的全部技術特征”,并以“不可替代的實質性作用”佐證被訴方行為對侵權結果產生的唯一性。區別于“控制或指導”標準對多主體關聯關系的強調,“不可替代的實質性作用”規則將視角轉向侵權結果的形成邏輯,在明確無辜消費者不擔責和專利權利益亟待維護的前提下,以價值評判為指引找尋法律規范,依據客觀的侵權事實反推侵權原因,最終聚焦于多主體對侵權結果的實質貢獻度。可以看出,我國司法總結的判定規則優勢在于,能夠借助事實和價值二元結合,確保裁判結果兼具形式正義和實質正義,避免“控制或指導”標準過度倚重法律判斷而衍生的價值失衡問題,然而這一優勢同樣也限制該規則的適用擴張,因其依賴涉訴產品在方法專利侵權中所發揮的不可替代作用,假若某主體引誘第三方實施方法專利侵權,并未以提供產品的形式固化方法專利內容,那么就難以追究該主體的侵權責任。
三、模式省思:多主體實施方法專利侵權的判定困境
(一)“單一實體規則”限制直接侵權適用
“單一實體規則”是指涉訴專利的全部技術特征均由單個主體實施,才能認定專利直接侵權。 “單一實體規則”是全面覆蓋原則的隱含條件,之所以限制直接侵權的主體數量,是因為無意思聯絡的不同主體會因客觀巧合,使單獨行為的疊加符合技術方案的全部特征,如果允許專利權人不加區分的主張權利,勢必引起專利權的過度擴張與公共利益的不當減損。美國法院不斷調適多主體實施方法專利的侵權判定標準,就是想既不脫離“單一實體 規則”承載的制度理性,又能實現規制不法行為的價值理性。
然而,從美國司法實踐來看, “單一實體規則”仍嚴格限制了直接侵權的適用空間。在“單一實體規則”的制約下,適用直接侵權會加劇權利人的舉證難度,專利權人不僅要證明多主體未經許可實施方法專利,還要證明被告對每一個主體實施的行為均具有控制力,嚴苛的證明責任阻卻權利人的救濟實效。雖然在我國多主體實施方法專利案件中,被訴方鮮用“單一實體規則”抗辯,但有學者認為“單一實體規則”恐怕是被訴方免責的關鍵所在[8]。
(二)政策性司法異化難以協調多方利益
知識產權內生于政治活動, 自制度締造之日起就帶有公共政策的色彩[9],專利制度也不例外。理想狀態的政策性司法能夠在法律框架下實現社會利益的最優解。現實生活中,受制于剛性的法律制度和復雜的案件情況,司法機關很容易高度依賴公共政策進行法律解釋,存在被功利主義或者社會本位思想單向侵蝕的危險,從而喪失司法本身的獨立價值。
多主體實施方法專利侵權判定規則的塑造過程,就是不同利益群體相互角逐與爭斗的過程,維系多方利益的平衡始終是司法裁判考量的核心要素。美國法院在判定思路上猶疑不定,正是因為過度依賴公共政策,沒能合理均衡各方利益。具體而言,依據美國多主體實施方法專利侵權判定標準的流變,將其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美國法院受制于社會本位理念,重視社會公眾利益而輕視方法專利的保護需求,確立了較為剛性的“控制或指 導”標準;第二階段,在功利主義理論的主導下,美國法院轉而摒棄“控制或指導”標準,以顛倒侵權責任認定形式為代價,采用引誘侵權的判定標準;第三階段,美國法院嘗試將功利主義理念嫁接到社會本位思想之上,軟化既有的“控制或指導”標準,但實際沒有脫離社會本位思想的單向控制,“控制或指導”標準的適用仍過于狹窄。在我國,騰達案的判決體現了政策性司法的積極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在功利主義理念指導下綜合社會本位思想,保證了判決結果的形式正義和實質正義。
(三)技術發展亟待更為合理的判定標準
信息技術的加持下,多主體侵犯方法專利的場所脫離傳統制造行業,轉向新興的生物制藥、交互式發明、物聯網設備等領域。在這些領域中,方法專利實施主體的地域更加分散,其通常隱藏于網絡設備后臺,無形操縱其他主體或者普通消費者實施方法專利侵權,缺乏控制或指導的關聯性,出現專利權人無法追責的法律困境。
現有的判定標準不足以滿足技術變革帶來的強烈需求,多主體實施方法專利侵權判定問題亟待更為合理的解決方案。首先,“控制或指導”標準無法提供準確的法律預期。“控制或指導”標準要求多主體間具有較高程度的聯系,卻未采用規范性要件框定聯系的范圍,模糊性的邊界阻礙新興技術的創新探索,甚至產生行為人趁機逃避責任的副作用[10]。其次, “不可替代的實質性作用”規則缺乏反復適用的基礎。“不可替代的實質性作用”規則僅限定于“為無辜第三方實施侵權提供實質性內容”類型的多主體侵權,狹窄的適用空間限制該規則的廣泛應用。主審該案的法官也認為,網絡通信技術的發展會帶來更為復雜的情況,需要不斷運用司法智慧確立合理的判定標準[11]。
四、路徑重塑:多主體實施方法專利的間接侵權證成
(一)解釋層面專利間接侵權的獨立性適用
傳統專利法律制度主要保護產品專利不受侵害,在制度設計時未充分考察方法專利的特殊性,致使多主體實施方法專利侵權的判定,既難以機械套用全面覆蓋原則適用專利直接侵權,也無法借助共同意思聯絡認定專利共同侵權。“控制或指導”標準和“不可替代的實質性作用”規則的適用局限同樣證明,擴張解釋直接侵權不足以扭轉方法專利“弱保護”的趨勢。從實踐觀之,多主體實施方法專利侵權的基本模式是引誘他人實施侵權或者提供專用品、設定編程等方式幫助他人侵權,因此,采用專利間接侵權的判定路徑更貼合多主體實施方法專利侵權的基本特征。
從法解釋的角度分析,反對論者所強調的專利間接侵權必須以專利直接侵權為前提,在我國并非絕對不可例外之選項。我國專利間接侵權的立法模式以美國法為藍本[12] ,逐步確立了專利幫助侵權和專利誘導侵權的二元模式。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釋中采用了“提供給他人實施了侵犯專利權的行為”以及“誘導他人實施了侵犯專利權的行為”等文本表述,似乎將“實施了”侵權行為視為間接侵權的要件之一。但制定者隨后澄清,該規則并不意指間接侵權的認定必須以直接侵權判決成立為前提[13]。事實上,專利間接侵權的規制對象是被控主體的“提供”和“誘導”行為,即實質性促使他人實施涉案專利全部技術特征的行為,至于是否存在法律意義上的直接侵權,并非認定間接侵權不可或缺的考量因素。從文義解釋和目的解釋的角度出發,上述條款中“實施了”的法律涵義應理解為已經實施或者正在實施的事實狀態[14] ,與此相對的直接侵權行為僅具備應然層面的發生可能性即可。
此外,域外國家諸如德國、法國等基本采納間接侵權獨立適用的模式[15]。而美國之所以奉行專利間接侵權的從屬性,緣由在于其以嚴格責任作為直接侵權的歸責原則,被控主體一旦實施涉案專利全部技術特征,就順理成章地考察間接侵權適用與否。根植于法律背景和制度建構的差異,我國直接侵權判定須考察行為人的主觀意圖,生產經營目的是直接侵權的先決要件。過分強調間接侵權的依附屬性就等同于變相承認,只要實施者缺乏生產經營目的,幫助者或誘導者就當然免責,這顯然偏離了間接侵權制度的初衷。
(二)價值層面專利間接侵權的合理性優化
審視多主體實施方法專利的侵權結構,可以發現其裹挾了權利人、潛在侵權主體、普通消費者、社會公眾等多方利益訴求。單純以司法政策為指引而不均衡考慮案件實際情況,法院很難處理好多主體間復雜的利益牽扯,造成案件預想結果與實際效果的脫節。一方面,專利強保護政策下,司法的內在功利主義傾向,驅使其注重維護專利權人利益,卻選擇性忽視社會福祉,引發“訴訟投機”“專利海盜”等一系列創新危機[16];另一方面,為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司法裁判謹慎地劃定專利保護邊界,倚仗社會政策的司法裁判滑向另一種極端,權利本位逐步淪為社會本位的附庸。
多主體實施方法專利侵權的特殊利益糾葛,要求法院審理案件時不能將目光偏向某一隅,有必要關聯耦合功利主義理念和社會本位思想,以兼具經濟效用和社會理性的“經濟社會規劃論” [17],作為多主體實施方法專利侵權判定的價值導向。“經濟社會規劃論”的實踐意義,就是審判者暫時性擱置各類訴求,依循統籌專利權人和公共利益保護的主線,結合案件事實進行價值層面的判斷,確保結果的實質正義,進而在案件事實與法律規范之間流轉反復,得到最為妥適的解決方案。騰達案正是遵循“經濟社會規劃論”的一般思路,綜合平衡專利權人、終端用戶、被控主體以及社會公眾等各方利益,以理性的價值評價引領該案的裁判過程。
法解釋視角能夠提供專利間接侵權獨立適用的依據,但“不受限制的適用引誘侵權,會導致專利間接侵權的濫用”。如果專利直接侵權和專利間接侵權完全脫鉤,較低的訴訟門檻可能引發專利權人的大規模訴訟,不僅如此,法院在司法審判中也會偏向適用要素簡明的間接侵權,發生向間接侵權“裁判逃逸”的現象。從“經濟社會規劃論”的理論內涵出發,獨立適用間接侵權不代表其脫離直接侵權的束縛,專利間接侵權并非完全獨立、全部獨 立,而應是有限獨立。這種有限性為獨立適用間接侵權預設了一種最低限度,即要以直接侵權的發生可能性或者專利權人的實際利益受損為前提,同時也必須將其限定在法律規定的特殊情形,防止專利間接侵權的泛化適用。
(三)規范層面專利間接侵權的定型化例外
法諺云:“一切規定,莫不有其例外。”[18]用以防止法律僵化而例外性適用間接侵權的判例,在司法實踐中并不鮮見。例如,根據北京高級人民法院《專利侵權判定指南(2017)》第119條的規定,直接侵權的實施主體因非生產經營目的或者構成專利法第六十九條第(三)項至第(五)項事由的,不影響間接侵權人的責任認定。多主體實施方法專利是特定技術條件與特殊法律背景相互交叉所衍生的特殊侵權,單獨為其構建專利保護制度立法成本太高,延伸適用現有規則又容易造成沖突,合理路徑是通過法律擬制的方式,將多主體實施方法專利侵權,定型化為一類獨立適用間接侵權的例外事由,并細化構成要件以保證司法判定的規范性。
具體而言,多主體實施方法專利的間接侵權定型化應滿足以下要件:
首先,在主觀要件上。一方面,行為人“以生產經營為目的”幫助或誘導其他主體實施方法專利侵權,“以生產經營為目的”著重考察行為人的主觀意圖,無需判斷實際營利情況;另一方面,行為人主觀“明知”其所實施的行為系幫助或誘導行為。從減輕權利人舉證責任的角度考量,“明知”應解釋為“推定明知”[19] ,允許用相反證據予以推翻。
其次,在客觀要件上。在適用方法專利幫助侵權時,提供物品的行為對侵權結果的形成“不可或缺”或者“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且物品除用于方法專利侵權外無其他合理的經濟和商業用途,排除技術中立的干擾。有法院認為,專利幫助侵權的認定,須將物品要件限定于“專用品”⑧ 。事實上,如果將幫助侵權的物品要件嚴格限于“專用品”,會嚴重妨礙專利間接侵權的適用。美國法院雖然在幫助侵權中要求物品的專用性,但會通過專利引誘侵權規制普通物品的提供行為[20]。日本則直接將侵權物品范圍從“專用品”擴展至“多功能 用途”[21]。因此,有學者指出,例外性適用間接侵權時,侵權物品的范圍就不再局限于“專用品”的范疇[22]。在適用方法專利誘導侵權時,誘導行為實質性促使其他主體或無辜第三方實施方法專利,其違法性的本質是實質性推動了專利侵害結果的形成。
最后,在法律后果上。多主體實施方法專利的間接侵權判定,不要求法律意義上的專利直接侵權 成立,發生以下兩種法律后果時可以獨立適用間接侵權。其一,事實層面方法專利的技術特征被全部實施,專利權人的利益遭受等同于專利直接侵權的損害,卻受制于制度原因無法追責到具體行為人, 例如實施侵權的主體是多個主體或者具備“非生產經營目的”的個人。其二,雖然尚未造成直接侵權損害,但存在直接侵權的發生可能性,從“經濟社會規劃論”的角度出發,“可能性”的范疇不宜寬泛,應采用“蓋然性”裁判觀念,將直接侵權發生可能性限定在“終將發生”[23]。
五、結論
多主體實施方法專利侵權是基于方法專利特殊性所引發的一類新型侵權,無論是適用民法共同侵權理論抑或是擴張性解釋專利直接侵權邊界,都難以實現對該侵權行為的有效規制。結合本國實際出發,將多主體實施專利定型化為一類適用專利間接侵權的特殊類型,具有法解釋上的正當性。為防止間接侵權的適用泛化,要進一步細化多主體實施方法專利侵權的主觀要件、客觀要件以及法律后果,并佐之經濟社會規劃論的司法價值引領,提高對方法專利的保護實效。
注釋:
① 參見Shields v. Halliburton Co., 493 F. Supp. 1376. 1389 (W.D. La. 1980)。
② 參見Faroudja Labs., Inc. v. Dwin Elecs., Inc., No. 97-20010 SW, 1999 WL 111788. at *6 (N.D. Cal. Feb. 24. 1999)。
③ 美國聯邦巡回法院在 2005年的Cross Medical Products v. Medtronic Sofamor Danek案依據“控制或指導”標準認定被告的方法專利侵權不成立,但在 2006年的On Demand Machine Corp. v. Ingram Industries案卻重新采用“某種聯系”標準推翻了下級法院的裁定。參見Cross Med. Prods. v. Medtronic Sofamor Danek, Inc., 424 F.3d 1293. 1311(Fed. Cir. 2005) ;On Demand Mach. Corp. v. Ingram Indus., 442 F.3d 1331. 1345 (Fed. Cir.2006)。
④ 參見 BMC Res., Inc. v. Paymentech, L.P., 498 F.3d 1373. 1379-81 (Fed. Cir.2007)。
⑤ 參見Muniauction, Inc. v. Thomson Corp., 532 F.3d 1318. 1329 (Fed. Cir. 2008)。
⑥ 參見Akamai Techs., Inc. v. Limelight Networks, Inc., 692 F.3d 1301. 1306 (Fed.Cir. 2012), rev'd, 132 S. Ct. 2111 (2014)。
⑦ 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知民終147號民事判決書。
⑧ 參見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7)京民終454號民事判決書。
參考文獻:
[1] 管育鷹. 軟件相關方法專利多主體分別實施侵權的責任分析[J]. 知識產權, 2020(03):3-16.
[2] Mark A Lemley, David O ’ Brien, Ryan M Kent. Divided Infringement Claims[J]. 33 AIPLA Q. J. 255 (2005).
[3] 張澤吾. 方法專利分離式侵權判定研究[J]. 法學雜志, 2016.37(03):62-69.
[4] 馬云鵬. 方法專利權利要求的解釋及使用環境因素的考量——以華為訴中興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案為例[J]. 中國發明與專利, 2016(05):94-98.
[5] Lickteig, S K, madess to the method: fixing the joint infringement system for method patents after akamai technologies, inc. v. limelight networks[J]. University of Illinois Journal of Law: Technology & Policy, 2015(1):39- 102.
[6] Jingyuan Luo . Shining the Limelight on Divided Infringement: Emerging Technologies and the Liability Loophole [J]. 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 30. no. Annual Review, (2015): 675-724.
[7] 李秀娟. 多方參與多步驟方法專利侵權判定——美國的判例與實踐[J]. 科技與法律, 2011(04):64-67+73.
[8] 王寶筠. 方法專利的侵權主體問題探討[J].中國發明與專利, 2018.15(11):80-86.
[9] 施小雪. 公共政策理論視角下我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實踐邏輯[J]. 知識產權, 2022(02):66-85.
[10] 何鵬. 方法專利拆分侵權認定規則的最新發展——美國法的實踐及對我國的啟示 [J ] .科技與法律, 2013(03):31-36.
[11] 張曉陽. 多主體實施方法專利侵權案件的裁判思路與規則——以敦駿公司訴騰達公司案為例[J]. 人民司法, 2020(07):35-40.
[12] 張其鑒. 我 國專利間接侵權立法模式之反思—— 以評析法釋〔2016〕1號第21條為中心[J].知識產權, 2017(04):35-41.
[13] 宋曉明, 王闖, 李劍. 《關于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的理解與適用[J]. 人民司法(應用), 2016(10):28-36.
[14] 吳漢東. 專利間接侵權的國際立法動向與中國制度選擇[J]. 現代法學, 2020.42(02):30-45.
[15] 張韜略. 跨境實施專利的侵權認定: 以德國法為視角 [J]. 知識產權, 2020(12):80-90.
[16] 張體銳. 專利海盜投機訴訟的司法對策[J].人民司法, 2014(17):108-111.
[17] 張體銳. 商業尋租與專利制度: 經濟社會規劃策略研究 [J]. 學術界, 2014(06):83-89+307.
[18] 易軍. 原則/例外關系的民法闡釋[J].中國社會科學, 2019(09):68-91+205-206.
[19] 李揚. 幫助型專利權間接侵權行為的法律構成[J]. 人民司法(應用), 2016(16):49-52.
[20] [美]謝科特, 托馬斯著. 專利法原理(第二版)[M]. 余仲儒譯. 北京: 知識產權出版社, 2016:253.
[21] 何培育, 蔣啟蒙. 回歸抑或超越: 專利間接侵權與共同侵權理論之辨[J]. 知識產權, 2019(05):46-57.
[22] 郭小軍. 多主體實施方法專利侵權的解決路徑——兼評“不可替代的實質性作用”規則[J].電子知識產權, 2020(09):55-66.
[23] 蔡元臻. 專利間接侵權制度專門化研究[J]. 中外法學, 2021.33(05):1227-1245.
中企檢測認證網提供iso體系認證機構查詢,檢驗檢測、認證認可、資質資格、計量校準、知識產權貫標一站式行業企業服務平臺。中企檢測認證網為檢測行業相關檢驗、檢測、認證、計量、校準機構,儀器設備、耗材、配件、試劑、標準品供應商,法規咨詢、標準服務、實驗室軟件提供商提供包括品牌宣傳、產品展示、技術交流、新品推薦等全方位推廣服務。這個問題就給大家解答到這里了,如還需要了解更多專業性問題可以撥打中企檢測認證網在線客服13550333441。為您提供全面檢測、認證、商標、專利、知識產權、版權法律法規知識資訊,包括商標注冊、食品檢測、第三方檢測機構、網絡信息技術檢測、環境檢測、管理體系認證、服務體系認證、產品認證、版權登記、專利申請、知識產權、檢測法、認證標準等信息,中企檢測認證網為檢測認證商標專利從業者提供多種檢測、認證、知識產權、版權、商標、專利的轉讓代理查詢法律法規,咨詢輔導等知識。
本文內容整合網站:中國政府網、百度百科、搜狗百科、360百科、最高人民法院、知乎、市場監督總局 、國家知識產權局、國家商標局
免責聲明:本文部分內容根據網絡信息整理,文章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向原作者致敬!發布旨在積善利他,如涉及作品內容、版權和其它問題,請跟我們聯系刪除并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