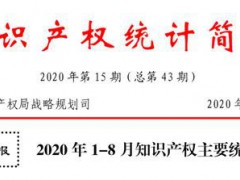“本文對于無效宣告程序的質證環(huán)節(jié)中對證據(jù)證明力的質證方面做一些基本介紹。”
在本系列的上一篇《專利無效宣告程序中專利權人應對篇(二)——證據(jù)“三性”的質證》中,介紹了在專利授權后的無效宣告行政程序中,介紹了對于證據(jù)的關聯(lián)性、合法性、真實性的質證,本篇重點討論對證據(jù)證明力的質證。
一、常見的質證重點
根據(jù)《專利審查指南》第四部分第八章第4.3.2節(jié)的規(guī)定,“在無效宣告程序中,一方當事人明確認可的另外一方當事人提交的證據(jù),專利復審委員會應當予以確認。但其與事實明顯不符,或者有損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者當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證據(jù)足以推翻的除外。”
因此,對于每一份證據(jù),都建議當事人仔細審核,不要輕易認可。
除了證據(jù)的“三性”以外,在無效宣告程序中,由于大多數(shù)時候,無效請求人提交的證據(jù)往往用于證明涉案專利的權利要求不具備新穎性或創(chuàng)造性,因此,實踐中當事人在證據(jù)證明力上爭奪較多的方面包括:證據(jù)是否能證明技術方案已經(jīng)公開、是否能證明公開時間在涉案專利申請日之前、證據(jù)是否屬于公知常識性證據(jù)等。
應注意的是, 在無效宣告程序中,合議組采用的是“優(yōu)勢證據(jù)”原則,根據(jù)《專利審查指南》第四部分第八章第4.3節(jié)的規(guī)定,“雙方當事人對同一事實分別舉出相反的證據(jù),但都沒有足夠的依據(jù)否定對方證據(jù)的,專利復審委員會應當結合案件情況,判斷一方提供證據(jù)的證明力是否明顯大于另一方提供證據(jù)的證明力,并對證明力較大的證據(jù)予以確認。”
因此,我們在質證的時候,如果能提供更有說服力的反證,也是很好的途徑。
二、證據(jù)是否作為現(xiàn)有技術公開
在無效程序中,最常見的證據(jù)是那些作為現(xiàn)有技術提交的證據(jù)。
《專利審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三章第2.1.2節(jié)規(guī)定:“現(xiàn)有技術公開方式包括出版物公開、使用公開和以其他方式公開三種,均無地域限制。”
在收到對方提交的證據(jù)時,應考慮不同的證據(jù)公開形式,仔細審查每一份證據(jù)是否滿足專利法意義上的公開,即,任何人想獲知就能夠獲知。
1. 對于出版物公開
《專利審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三章第2.1.2.1節(jié)規(guī)定了出版物公開的情況:“專利法意義上的出版物是指記載有技術或設計內容的獨立存在的傳播載體,并且應當表明或者有其他證據(jù)證明其公開發(fā)表或出版的時間。
……
出版物不受地理位置、語言或者獲得方式的限制,也不受年代的限制。出版物的出版發(fā)行量多少、是否有人閱讀過、申請人是否知道是無關緊要的。
印有“內部資料”、“內部發(fā)行”等字樣的出版物,確系在特定范圍內發(fā)行并要求保密的,不屬于公開出版物。”
下面兩個案例中,雖然請求人提交了出版物/印刷品作為證據(jù),但是卻最終沒有被認定為在專利申請日之前就處于公開狀態(tài)。
【案例一——(2014)高行終字第1442號】該案中,請求人提交的證據(jù)是一本圖書,但是封底印有“內部發(fā)行”字樣,因此即使該圖書為正規(guī)出版物,并且請求人還提供了該圖書收藏在國家圖書館可被公眾借閱的文獻復制證明,最終仍被認為“沒有證據(jù)表明在專利的優(yōu)先權日之前該證據(jù)處于公開狀態(tài)”。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改革開放之前和之初,技術交流封閉保守,很多涉及國計民生的技術甚至處于絕對保密狀態(tài),即使印制成書,也是不對社會公眾放開購買的。具體來說,在我國圖書發(fā)行歷史上,約50年代到80年代,確實存在過內部發(fā)行制度,內部發(fā)行的圖書僅限經(jīng)過批準的特定人群購買,并且購買者有義務妥善保管圖書,不使其流入社會。這類圖書是不符合專利法意義上的公開的。因此,在核對技術圖書類證據(jù)時,遇到年代較早的圖書,如果仔細翻閱封面、封底等處,也許會有驚喜。
【案例二——第41813號無效決定】該案中,某份證據(jù)是請求人公司的產(chǎn)品宣傳手冊,封底印有“2016年4月印刷”字樣。復審委認為,其屬于企業(yè)自行印制的廣告宣傳資料,不具備法定公開出版物那樣嚴格的出版發(fā)行審批程序,沒有正規(guī)出版物ISBN標準書號,印制具有一定的隨意性和不確定性,包括印刷時間、地點、承印人、發(fā)行方式、公開范圍等。因此,未認可該宣傳手冊上的內容為公開的現(xiàn)有設計。
由該案例可見,雖然《專利審查指南》中對于出版物的外延規(guī)定包括多種形式的印刷品,其中就包括產(chǎn)品目錄、廣告宣傳冊等。但是顯然,這些非正規(guī)出版物的證明力是不如正規(guī)出版的圖書的。在實踐中如果遇到這些出版物,大可以嘗試質疑其是否真正被公開。
2. 對于使用公開
《專利審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三章第2.1.2.2節(jié)規(guī)定了使用公開的情況:“由于使用而導致技術方案的公開,或者導致技術方案處于公眾可以得知的狀態(tài),這種公開方式稱為使用公開。
使用公開的方式包括能夠使公眾得知其技術內容的制造、使用、銷售、進口、交換、饋贈、演示、展出等方式。只要通過上述方式使有關技術內容處于公眾想得知就能夠得知的狀態(tài),就構成使用公開,而不取決于是否有公眾得知。但是,未給出任何有關技術內容的說明,以致所屬技術領域的技術人員無法得知其結構和功能或材料成分的產(chǎn)品展示,不屬于使用公開。
如果使用公開的是一種產(chǎn)品,即使所使用的產(chǎn)品或者裝置需要經(jīng)過破壞才能夠得知其結構和功能,也仍然屬于使用公開。此外,使用公開還包括放置在展臺上、櫥窗內公眾可以閱讀的信息資料及直觀資料,例如招貼畫、圖紙、照片、樣本、樣品等。”
由以上規(guī)定可見,使用公開的形式多種多樣,而是否構成使用公開的重點在于有關技術內容是否處于“公眾想得知就能夠得知的狀態(tài)”。
【案例三——(2018)京73行初5687號】在該案中,涉及對從國外知名視頻分享網(wǎng)站Youtube下載的視頻是否構成使用公開的認定。請求人提交了經(jīng)過公證認證的Youtube視頻,但是該視頻的公開方式選項被設置為“unlisted”狀態(tài)。經(jīng)查,Youtube視頻可以由用戶設置訪問權限,可以是“私享(private)”、“不公開(unlisted)”或“公開(public)”。“私享(private)”只允許用戶自己和用戶指定好友訪問視頻;“不公開(unlisted)”狀態(tài)下只有獲得視頻URL地址的人可以訪問視頻;而“公開(public)”狀態(tài)下則允許任何人訪問視頻。因此,該證據(jù)中的視頻由于公開方式選項是設置為“unlisted”狀態(tài)的,最終被認定為僅針對特定人公開,并非處于“為公眾所知”的狀態(tài),不能作為現(xiàn)有技術用于評價涉案專利的創(chuàng)造性。
【案例四——(2019)京73行初7880號】該案同樣涉及Youtube視頻作為證據(jù)的情況。在無效階段,復審委未認可該證據(jù)作為現(xiàn)有技術公開,理由是,YouTube視頻可以由用戶設置訪問權限(即“私享(private)”、“不公開(unlisted)”或“公開(public)”),因此即使公證時顯示該視頻狀態(tài)為“公開(public)”,但無法確定某一視頻的訪問權限是否被更改過。而在行政訴訟階段,法院合議庭認為,在專利行政糾紛中對網(wǎng)絡視頻發(fā)布時間、公開與否的判斷,應當以公證書公證的視頻情況為準,除非相對方提出證據(jù)證明該視頻的內容、隱私設置曾發(fā)生過變化以致于該視頻的內容及公開狀態(tài)不穩(wěn)定。因此推翻了復審委的證據(jù)認定。
【案例五——(2019)京73行初15734號】該案中,請求人提供了證據(jù)鏈,擬證明某型號空調在申請日前公開銷售,但是,其中公證購買的該型號空調是二手市場購買的,該空調的底殼銘牌旁和面板上粘貼的兩個條形碼不一致,因此,最終認定,根據(jù)現(xiàn)有證據(jù)無法證明該二手空調是否被改裝過結構,無法確認其原始結構,所以不構成使用公開。
【案例六——(2019)京73行初9422號】該案中,請求人為了證明專利申請日前就已經(jīng)銷售相同產(chǎn)品,提供了產(chǎn)品采購合同。然而,采購合同中顯示,該產(chǎn)品為委托方提供技術方案的定制產(chǎn)品,且定有保密條款,約定生產(chǎn)方應負保密責任。因此,該采購合同中的產(chǎn)品不處于公眾想得知就能得知的狀態(tài),不構成使用公開。
【案例七——(2018)京73行初4220號】該案中,請求人提供了銷售發(fā)票和勞務清單,能夠證明某型號產(chǎn)品已經(jīng)在先銷售;但關于該型號產(chǎn)品的內部結構,僅提供了一些自制證據(jù),包括產(chǎn)品圖片、設計圖紙、公司型號編排規(guī)定等,無法確認其真實性和形成時間,因而不能確認該型號產(chǎn)品的具體內部結構,無法視為使用公開。該案判決書中還強調了,“行政訴訟的證據(jù)證明標準應當是達到‘證據(jù)確鑿’的程度,即待證事實應當具有高度可能性”。
【案例八——(2019)京73行初15771號】該案中,請求人提供的某份證據(jù)記載了公證人員前往某一住戶家中對其家中擺放的餐椅及該住戶出示的某家居城銷售單進行了拍照,擬證明該餐椅已經(jīng)在先銷售即使用公開。但是法院認為,證據(jù)中所拍攝對象的來歷不明,公證過程也無法判斷所拍攝對象的來源問題、銷售單系手寫單據(jù),僅為上述住戶出示,年代久遠并且字跡模糊不易辨認,且僅為文字銷售憑據(jù),其上無任何圖片信息與所拍攝對象相對應。最終認為該證據(jù)無法構成使用公開。
由以上案例可見,無論證據(jù)要證明的是出版物公開還是使用公開,質證時都應該關注該證據(jù)是否真正在涉案專利申請日之前“公開”了;而證明標準采用“高度蓋然性準則”,根據(jù)證據(jù)各個方面綜合判斷其是否高度可能在先公開,并非嚴格要求該證據(jù)百分之百的絕對可能處于公開狀態(tài)。
三、證據(jù)的公開日
在第二部分中已經(jīng)討論了如何判斷一份作為現(xiàn)有技術的證據(jù)是否滿足“公開”的要求。在證據(jù)滿足“公開”的要求的前提下,應進一步判斷證據(jù)的公開日,是否在涉案專利的申請日/優(yōu)先權日之前,因為只有公開在前,才是專利法意義上的現(xiàn)有技術。
1. 出版物的公開日
出版物的公開日相對來說較為明確,一般會標注在出版物的著錄頁上。但是,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例如,《專利審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三章第2.1.2.1節(jié)規(guī)定了:“出版物的印刷日視為公開日,有其他證據(jù)證明其公開日的除外。 印刷日只寫明年月或者年份的, 以所寫月份的最后一日或者所寫年份的12月31日為公開日。”
【案例九——第15409號無效決定】該案中,涉案專利的申請日為2005年1月11日,證據(jù)的公開日寫的是2005年1月,因此,該證據(jù)的公開日被認定為2005年1月31日,晚于申請日,無法作為現(xiàn)有技術使用。
【案例十——第41068號無效決定】該案中,證據(jù)(圖書)的著錄頁注明:“2014年3月第1版,印次:2017年7月第5次印刷”。涉案專利的申請日是2014年,因此,根據(jù)《專利審查指南》相關規(guī)定,該證據(jù)被認為在申請日之后公開,無法作為現(xiàn)有技術使用。
【案例十一——第20165號無效決定】該案中,請求人提交的證據(jù)(圖書)的印刷日(第7次印刷)同樣在涉案專利的申請日后,但是,請求人在口審辯論終結前還提交了蓋有“國家圖書館科技查新中心”紅章的該證據(jù)第1次印刷的同版復印件,用以證明該書已于涉案專利申請日前公開。經(jīng)核實,專利復審委員會認為,該證據(jù)兩次印刷的內容相同,由此可見,該證據(jù)中除版權頁之外的內容已于第1次印刷日公開,因此可以作為現(xiàn)有技術使用。
2.使用公開的公開時間
《專利審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三章第2.1.2.2節(jié)規(guī)定了使用公開的公開日:“使用公開是以公眾能夠得知該產(chǎn)品或者方法之日為公開日。”
對于使用公開的證據(jù),需要根據(jù)具體情況判斷其公開日。一般來說,對于產(chǎn)品而言,公開銷售的日期可以作為使用公開日。
【案例十二——(2020)京73行初10464號】該案中,當事人主張以某產(chǎn)品的銘牌上的出廠日期為公開日,但是法院認為,產(chǎn)品銘牌上的出廠日期與產(chǎn)品的實際銷售日期之間并沒有必然的確定時間關系,因此不能作為使用公開的公開日。
【案例十三——(2019)京73行初10994號】與案例十二類似,該案中,當事人同樣主張以某產(chǎn)品的銘牌上的日期作為公開日,還提供了訂單、合同。但法院同樣認為,該銘牌上的日期僅能證明制造日,且訂單和合同與該銘牌信息無法對應,因此銘牌日期不能作為公開銷售日期,即不能作為使用公開的公開日。
在使用公開中,還有一種特殊的情形,即如果能夠通過反向工程獲知公開銷售的產(chǎn)品的內部技術方案,則該技術方案也認為已經(jīng)被公開。但應注意的是,在質證時,還應審核反向工程的技術手段是否是申請日前已經(jīng)存在的,如果該項技術手段是在申請日之后才出現(xiàn)的,則說明在申請日前,公眾無法對該產(chǎn)品進行反向工程,即無法獲得其內部技術方案,自然該技術方案也就無法被公眾獲知。
3.互聯(lián)網(wǎng)證據(jù)的公開日
《專利審查指南》第四部分第八章第5.1節(jié)“互聯(lián)網(wǎng)證據(jù)的公開時間”中規(guī)定:“公眾能夠瀏覽互聯(lián)網(wǎng)信息的最早時間為該互聯(lián)網(wǎng)信息的公開時間,一般以互聯(lián)網(wǎng)信息的發(fā)布時間為準。”
在實踐中,對于來自互聯(lián)網(wǎng)的證據(jù),一般會綜合考慮其網(wǎng)站運行機制、權威性等方面確定公開日。
【案例十四——(2018)京73行初4102號】該案中,當事人使用優(yōu)酷上網(wǎng)友上傳的介紹展覽會上展品的視頻作為證據(jù),主張視頻上傳日為公開日。對方當事人認為在優(yōu)酷網(wǎng)發(fā)布視頻時,用戶可以自主選擇是否公開,之后也可以自由更改設置,因此不能確定是否在上傳日就已經(jīng)公開。但是法院認為,已知展覽會于*年*月*日開幕,該展覽對公眾開放,結合視頻的標題,可以推斷該網(wǎng)友上傳該視頻是對該展覽會的記錄,其與網(wǎng)友分享該展覽會的可能性更大。在對方當事人未能提交充分反證的情況下,該視頻上傳時被公開的可能性要大于其所主張情形,故上傳時間即為公開時間存在高度蓋然性。即,法院認定視頻上傳日為公開日。本案例和案例四的事實認定相似,由此再次可知,證據(jù)認定采用的是高度蓋然性標準,并不要求排除所有微小可能。
【案例十五——第38854號無效決定】該案中,無效請求人提交了兩份證據(jù),一份是來自CSDN(知名IT論壇)的文章,另一份是來自個人網(wǎng)站的文章,兩份證據(jù)均顯示文章上傳日在涉案專利申請日之前。在決定中,復審委員會采納了來自CSDN的證據(jù),但對于來自個人網(wǎng)站的證據(jù)的公開日不予認可,因為該個人網(wǎng)站的權威性和運行機制無法確定。
4.其他方式的公開
《專利審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三章第2.1.2.3節(jié)規(guī)定了“以其他方式公開”:“為公眾所知的其他方式,主要是指口頭公開等。例如,口頭交談、報告、討論會發(fā)言、廣播、電視、電影等能夠使公眾得知技術內容的方式。口頭交談、報告、討論會發(fā)言以其發(fā)生之日為公開日。公眾可接收的廣播、電視或電影的報道,以其播放日為公開日。”
【案例十六——第51616號無效決定】該案中,請求人提交了從國際電信聯(lián)盟官方FTP上下載的某次會議提案,欲作為現(xiàn)有技術使用,但是該FTP上的該份會議提案的上傳日期在涉案專利申請日之后,請求人解釋說是因為FTP曾經(jīng)在申請日之后遷移過,因此日期不是原始上傳日期;同時,請求人提交證據(jù)證明了該會議在申請日之前召開。合議組認為,請求人的證據(jù)不能證明該提案的全部內容均在會議期間以口頭、文字或其他形式公開,處于能夠為公眾獲得的狀態(tài),因此對于會議日即為提案公開日的主張不予支持。
可見,相對于出版物公開方式,“其他方式公開”的公開日證明難度相對較大,因為不像出版物本身印有出版日,“其他方式公開”的公開日往往需要從其他角度挖掘可信度較高的證據(jù)/證據(jù)鏈,在質證時也更容易被挑戰(zhàn)。
此外,對于使用公開和以其他方式,在2008年《專利法》第三次修正以前,使用公開和以其他方式公開均是有地域限制的,即,需要在“國內”,2008年修法之后,上述兩種公開方式不再有地域限制。根據(jù)過渡辦法,申請日在2009年10月1日前的專利申請以及根據(jù)該申請授予的專利權,仍適用2000年《專利法》,即非國內的使用公開和以其他方式公開不作為現(xiàn)有技術使用。因此在質證時,如果遇到國外的使用公開或者以其他方式公開的相關證據(jù),還需注意涉案專利的申請日是否在2009年10月1日以后。
四、關于公知常識性證據(jù)的認定
《專利審查指南》第四部分第八章第4.3.3節(jié)“公知常識”中規(guī)定:“主張某技術手段是本領域公知常識的當事人,對其主張承擔舉證責任。該當事人未能舉證證明或者未能充分說明該技術手段是本領域公知常識,并且對方當事人不予認可的,合議組對該技術手段是本領域公知常識的主張不予支持。當事人可以通過教科書或者技術詞典、技術手冊等工具書記載的技術內容來證明某項技術手段是本領域的公知常識。”
在無效程序中,對于公知常識性證據(jù),提交期限為“在口審辯論終結前”(參見《專利審查指南》第四部分第三章第4.3節(jié)),也即,如果無效請求人在口審當庭才臨時提交了公知常識性證據(jù),專利權人就面臨著需要在口審時當庭質證的局面,不會有太多思考的時間。
對于對方當事人提交的“公知常識性證據(jù)”,除了和其他證據(jù)一樣需要檢查核對其三性、是否公開以及公開時間等之外,還需要重點核對該證據(jù)是否能夠歸類為公知常識性證據(jù)。如果該證據(jù)不屬于公知常識性證據(jù),則不能用于證明某特征是公知常識,甚至會因為提交期限不能享受公知常識性證據(jù)的特殊期限而作為超期證據(jù)被拒絕。
至于何為公知常識、什么樣的證據(jù)屬于公知常識性證據(jù),《專利審查指南》中并未給出明確定義,僅僅例舉了幾種公知常識的形式:“……公知常識,例如,本領域中解決該重新確定的技術問題的慣用手段,或教科書或者工具書等中披露的解決該重新確定的技術問題的技術手段。”(參見《專利審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四章第3.2.1.1節(jié))
因此在質證過程中,重點需要核對的是,對方提交的證據(jù)是否屬于教科書或工具書,工具書又包括技術詞典、技術手冊等。
【案例十七——(2020)最高法知行終35號】該案是復審后行政訴訟的案例,在復審過程中,復審決定在駁回涉案專利時引用了一份證據(jù)(書籍《腫瘤研究前沿》)作為公知常識性證據(jù)。在行政訴訟階段,法院持不同觀點,認為該證據(jù)不屬于公知常識性證據(jù),理由為該書不是教科書,具體來說,認為該書旨在介紹世界腫瘤研究的最新進展,并非講述腫瘤研究領域一般性技術知識,不屬于通常意義上教科書;且該書版權頁“內容簡介”記載,“本書可作為相關專業(yè)研究人員的參考用書,也可供高校、醫(yī)院的相關人員閱讀使用”,同樣表明其并非通常意義上的教科書,而是專業(yè)研究人員的參考用書。此外,該案中并未有其他證據(jù)表明,該書在相關領域已經(jīng)成為研究人員的普遍參考用書。最終,該證據(jù)被認定為并非公知常識性證據(jù)。
【案例十八——第54093號無效決定】該案中,無效請求人提交了某本圖書作為公知常識性證據(jù),合議組認為,請求人提交的頁面中沒有記載表明該書籍為教科書或工具書,且該書籍目錄中包括了“**應用新進展”和“**技術的新突破”等章節(jié),明顯不屬于本領域普通技術知識,因此不認可該證據(jù)作為公知常識性證據(jù)。
值得注意的是,在案例十七中,最高院在論理時認為:“相關技術領域公知常識的認定,直接決定了該領域普通技術人員所應具備的技術知識和認知能力,進而對創(chuàng)造性判斷具有重要影響。因此,對于公知常識的認定應該以確鑿無疑為標準,應該有充分的證據(jù)或者理由支持,不應過于隨意化。一般而言,對于相關技術知識是否屬于公知常識,原則上可以通過技術詞典、技術手冊、教科書等所屬技術領域中的公知常識性證據(jù)加以證明;在難以通過技術詞典、技術手冊、教科書等公知常識性證據(jù)予以證明的情況下,也可以通過所屬領域的多份非公知常識性證據(jù)例如多篇專利文獻、期刊雜志等相互印證以充分證明該技術知識屬于公知常識,但這種證明方式應遵循更嚴格的證明標準。其次,公知常識性證據(jù)是指技術詞典、技術手冊、教科書等記載本領域基本技術知識的文獻。如無相反證據(jù),技術詞典、技術手冊、教科書記載的技術知識可以推定為公知常識。對于技術詞典、技術手冊、教科書之外的文獻,判斷其是否屬于記載本領域基本技術知識的公知常識性證據(jù),則需要結合該文獻的載體形式、內容及其特點、受眾、傳播范圍等具體認定。”
即,上述觀點認為,對于公知常識的認定應該確鑿無疑,但是不應過于僵化地將公知常識限定在技術詞典、技術手冊、教科書記載的技術知識,也可以通過其他方式證明某項技術是公知常識。
實踐中,也會遇到當事人使用例如多篇專利文獻、期刊雜志等來共同作為用于證明公知常識的證據(jù)的情況,但值得注意的是,“用于證明公知常識的證據(jù)”比“公知常識性證據(jù)”范圍要廣。前者本身可以不是公知常識性證據(jù)(例如,僅是專利文獻),只是證明目的是要證明某技術是公知常識。但是后者本身的性質為教科書或工具書等公知常識性證據(jù)。區(qū)分二者的原因在于,首先,二者在無效程序中的提交期限不一樣,根據(jù)《專利審查指南》第四部分第三章第4.3節(jié),二者中僅公知常識性證據(jù)能夠延遲到口審時提交;其次,前者比后者的證明標準要求得更高。因此在質證中,對二者關注的方面也相應地有所不同。
五、結語及建議
本文對于無效宣告程序的質證環(huán)節(jié)中對證據(jù)證明力的質證方面做了基本介紹,并通過案例例舉了幾種情況,希望能夠對讀者有些幫助。
中企檢測認證網(wǎng)提供iso體系認證機構查詢,檢驗檢測、認證認可、資質資格、計量校準、知識產(chǎn)權貫標一站式行業(yè)企業(yè)服務平臺。中企檢測認證網(wǎng)為檢測行業(yè)相關檢驗、檢測、認證、計量、校準機構,儀器設備、耗材、配件、試劑、標準品供應商,法規(guī)咨詢、標準服務、實驗室軟件提供商提供包括品牌宣傳、產(chǎn)品展示、技術交流、新品推薦等全方位推廣服務。這個問題就給大家解答到這里了,如還需要了解更多專業(yè)性問題可以撥打中企檢測認證網(wǎng)在線客服13550333441。為您提供全面檢測、認證、商標、專利、知識產(chǎn)權、版權法律法規(guī)知識資訊,包括商標注冊、食品檢測、第三方檢測機構、網(wǎng)絡信息技術檢測、環(huán)境檢測、管理體系認證、服務體系認證、產(chǎn)品認證、版權登記、專利申請、知識產(chǎn)權、檢測法、認證標準等信息,中企檢測認證網(wǎng)為檢測認證商標專利從業(yè)者提供多種檢測、認證、知識產(chǎn)權、版權、商標、專利的轉讓代理查詢法律法規(guī),咨詢輔導等知識。
本文內容整合網(wǎng)站:中國政府網(wǎng)、百度百科、搜狗百科、360百科、最高人民法院、知乎、市場監(jiān)督總局 、國家知識產(chǎn)權局、國家商標局
免責聲明:本文部分內容根據(jù)網(wǎng)絡信息整理,文章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向原作者致敬!發(fā)布旨在積善利他,如涉及作品內容、版權和其它問題,請跟我們聯(lián)系刪除并致歉!